米我和妻子英格丽德在加纳的阿布里刚呆了一个多星期,我们的主人夸梅·奥本(Kwame Obeng)告诉我,第二天下午我将和皇家鼓手一起在酋长的宫殿里表演,庆祝一个重要的神圣日子。
我又不是毫无准备。我第一次见到奥本是在三年前,当时他来到多伦多指导一个由加纳移民和一个孤独的西方人(我自己)组成的鼓乐团。我们变得很亲密:奥本打电话给我米努在特维语中,也就是“我的兄弟”。特维语是阿肯族人的语言。一年后,当他的签证到期时,他邀请我回到家乡阿布里(Aburi)继续和他一起学习。阿布里是一个坐落在青翠的阿库阿佩姆山(Akuapem Hills)上的小镇。两年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现在是时候让他看看我的能耐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永远不会知道这对奥本来说是不是一个惊喜。
演出那天,奥本让我和他的侄子站在一对巨大的桶形雕塑前,他的侄子名叫夸梅·安特维(Kwame Antwi)bommaa并排站着的鼓。每一个bommaa雕像由镂空的5英尺长的树干雕刻而成,两尊雕像都被漆成光亮的黑色,并用红色天鹅绒包裹,并用黄铜饰钉固定。就在我们前面,在我们的左边,奥本站在一对巨大的酒杯形状的雕像前阿图潘有羚羊头的鼓。在我们后面,一个由年轻男孩和中年男子组成的四重奏,敲着三个小鼓和一个铁钟。他们是节奏部,而我和两个夸梅斯组成了前线。
我别无选择,只好鼓声坚持下去。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也在努力理解发生了什么。
演出开始时,夸梅·安特维和我开始用树枝做成的L形长棍猛击厚厚的牛皮头。我们真是天生一对:他又长又瘦又黑,我又矮又软又白。庭院另一端的高台上,逐渐挤满了身穿长袍和礼服的酋长和宫廷官员,这些衣服都有不同的颜色:绿松石、猩红、钴、栗色。几乎没有闲聊。相反,我们打鼓的时候,我们的观众静静地听着,各种名人站起来发表演讲,向他们的祖先祈祷。
大屏幕上播放着节奏bommaa鼓由两个鼓手同时演奏的几组图案组成,每一个图案都比上一个更长、更复杂。起初,我能够一杆接一杆地匹配安特维。但是当我们进入更长更复杂的材料时,事情完全偏离了轨道。突然,安特维似乎加入了我从未听过的节奏。我试着跟上他,模仿他的手的动作,即使我不太明白他在玩什么。
但我做不到。站在聚集在一起的皇室成员面前,我慢慢明白了真相:我本应该在阿布里公开演奏的节奏与奥本在多伦多教给我的不一样,而奥本在前一天的一次简短的私人课上为英格丽德和我重复了这些节奏。相反,这些节奏包括了大量的节奏这些材料与迄今为止他向我们展示的任何东西都截然不同;如此不同,以至于我无法在最激烈的时刻理解它们,更不用说执行它们了。但似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
“亚历克斯,怎么了?”休息时,我们俩在英格丽德旁边坐下,安特维问道。“你昨天打了这些,没有问题。”
“节奏是不同的,”我说,仍然震惊于我的首次公开亮相完全失败。
“什么?”
“这些节奏是不同的。他们不是我在多伦多打球的球队。它们不是我们昨天课上和奥本玩的那些。”
“当然是一样的,”安特维说。“只有更快!”
这将是我们加纳朋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的标准说法:节奏是一样的,只是更快了!但他们没有。当我们的主人继续坚持说他们教了我正确的节奏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搞砸了表演:在仪式上,在葬礼上,有时是在一大群人面前。我无法停止表演——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学习这种音乐,我们在合奏团的出现是奥本声望的源泉——但知道这一点的首领和宫廷官员们fontomfrom最好的肯定已经意识到我总是搞砸它,即使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只说:woaye正面!(“干得好!”)。
我别无选择,只好鼓声坚持下去。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也在努力理解发生了什么。最后我将其归结为两种选择:一种是我们对于什么构成了音乐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及是什么赋予了一段音乐独特的身份和听觉特征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或者奥本故意不让英格丽德和我看到完整的节奏,原因不明。这是欺骗还是精神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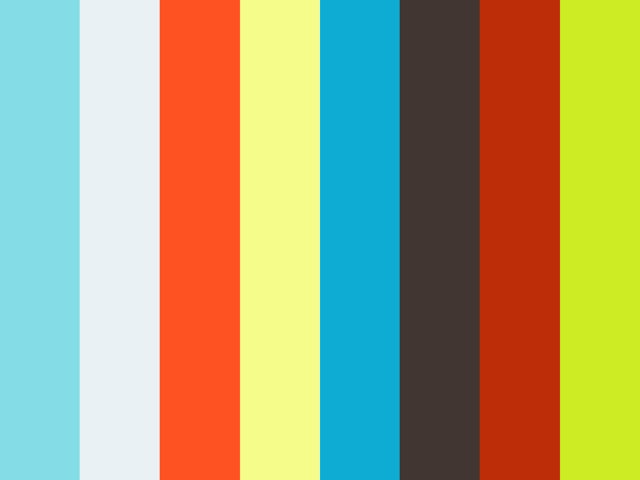
米如果我们演奏的是那种风格的音乐,我的困惑和突然的无能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fontomfrom,只是背景音乐,相当于鸡尾酒钢琴。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当酋长们因公务出现在公共场合时,王室的鼓声就会响起。他们是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权是办公室的主要装备。也许更重要的是,大bommaa和阿图潘鼓不仅仅是舞蹈的音乐。他们谈了。字面上。
Twi是一种声调语言,就像普通话一样:每个音节都有自己的音高,每个单词或短语都有自己独特的旋律。改变音调,改变旋律,单词的意思也会改变。像问一个人的名字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变成了一种鸟鸣练习。

通过模仿特维人的音调和节奏,阿肯人可以用他们的乐器“说话”——他们的喇叭和小号,他们的鼓和铃铛——几乎和他们用嘴说话一样清晰。的阿图潘,产生两个不同的音高,特别适合这项任务;但是,bommaa我也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宫殿里的人群如此安静的原因:他们在听鼓声要说些什么。这种现象被称为替代语言,在西非和中非都很普遍。它甚至可以为最简单的音乐增加一层语义深度。
例如,每当族长夸西娜娜(Nana Djan Kwasi)站起来绕着院子走的时候,夸米斯和我两个就会进行一场小小的呼救。
夸梅Obeng:物料清单
夸梅·安特维和我:BRRM BRRM !
有节奏的短语bom bom BRRM BRRM,bom bom BRRM BRRM它有一个很好的节奏,可以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填充,当首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然而,另一方面,是乐队主要的会说话的鼓手诚恳地恳求道:娜娜,bre正好!娜娜,bre正好!“酋长,慢点!酋长,小心点!”如果酋长在公共场合绊倒,那就是运气不好的迹象。所以我们要求他小心脚下。
鼓声不仅是对活着的人说的,也是对死去的人说的:那些离开尘世的受人尊敬的祖先们,仍然继续影响着他们家族的事务。阿肯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永远守护着他们,他们必须永远用祈祷、祭品和其他纪念品来安抚他们。他们还认为他们的祖先对鼓声特别敏感。这就是为什么阿肯族鼓手通常会非常小心地避免犯错的原因之一。你不会想说错话而激怒你的祖先吧。在过去,一个邋遢的皇家鼓手很可能会被割掉一只耳朵。所以,当我那天在皇宫里和安特维一起屠杀我的部分时,我不仅仅是让这个团体听起来很糟糕——我是在一个丰富的文化体系中插一把扳手,在这个文化体系中,语言、艺术和宗教都是交织在一起的。难怪当我从鼓声中走开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犯的错误的回声仍在院子里回荡。
这种音乐很重要。那么,为什么奥本坚持要隐瞒信息,这样我们在加纳的时候就不会搞砸几乎所有的演出了?他是不是别有用心?还是阿肯族音乐的某些基本方面让我们在文化、心理甚至神经层面上无法理解?

我ngrid和我都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生,1997年夏天我们去了加纳。我当时正在攻读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这是一种音乐人类学,而英格丽德正在攻读打击乐博士学位。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完全是音乐菜鸟。但是fontomfrom出乎意料,也非同寻常。
与西方非洲舞蹈课上经常伴随的鼓声不同,fontomfrom没有特别强的凹槽。但和大多数西非鼓乐一样,它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运动部件,不同于在地面上演奏的长而复杂的图案bommaa和阿图潘到短的,高度重复的模式演奏在较小的鼓和铁钟。所有这些节奏相互关联;通常,它们会相互补充,一个鼓的声音填补了其他鼓的沉默,产生意想不到的模式,就像挂毯上的单独的丝线。
Fontomfrom节奏也可以是奇怪的模糊。例如,你可能认为你在演奏华尔兹(一二三,一二三),而你旁边的人听起来像是在演奏进行曲(一二二,一二二)。事实上,如果你听他说的时间足够长,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决定你也真的在演奏进行曲。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fontomfrom合奏就像置身于埃舍尔平版版画的声波版中:当你将注意力从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时,整个画面似乎都发生了变化。
试图破译这些简短而令人困惑的片段就像试图接住一把落下的刀。
的bommaa然而,人们突然期望我在加纳打球的模式,在他们自己的联赛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一些并不只是节奏上的模糊;他们有节奏障碍。音乐学家会说它们是有韵律的,或者与任何一种稳定的脉搏缺乏明确的关系。但他们肯定是有逻辑的,因为每当两个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鼓手接手bommaa,他们不仅做到了完美的一致性;他们还以完美的一致性与其他鼓手的角色矩阵协调出入。显然,他们知道并听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英格丽德和我几乎听不到bommaa r一点也不奇怪。虽然我们通常与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庭鼓手搭档表演,但我们也经常被告知“更大声”、“更快”和“更有力”,这只会让我们更难理解搭档演奏的节奏(其他人也更容易听到我们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在其他情况下很容易做到:很难描述一个声音有多大fontomfrom整个乐团,伴随着铿锵的铁钟,刺耳的小鼓,轰鸣阿图潘,而且雷鸣般的bommaa.更糟糕的是,夸西娜娜的宫殿庭院是一个巨大的回音室。我们录下了在法庭上的每一次表演,但大鼓在混凝土墙壁和波纹金属屋顶上弹跳的声音完全超载了我们的麦克风,把我们所有的录音变成了咆哮的混乱。
在我们的停留快结束时,Nana Djan Kwasi法庭的一位友好的副长官允许我们在附近一个村庄的更可控的条件下录制Obeng和其他皇家鼓手。在这些磁带的帮助下,英格丽德几乎把节奏降下来了。她一边听着,一边低声唱着:“哒、哒、哒、哒、哒、哒……”
“嘿,艾尔,这真的开始有意义了!”我现在可以理解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了
“我也是,”我说。“但还是有一些地方让我无法理解。”
“你是说像这里?”英格丽德说,给了我一段带子。
“是的,”我微微眯起眼睛说。“那是什么鬼东西?”
西方音乐随着自己的记谱系统而发展,所以西方音乐家倾向于听他们能读到的,读他们能听到的。它的演变并没有反映出fontomfrom. 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很短的片段bommaa我们无法准确记录的节奏;就我们的音乐系统而言,它们并不存在。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听不清他们的声音:他们听起来很模糊,就像印象派风景画中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问题不在我们的耳朵,而在我们的大脑。
心理学家比尔·汤普森澳大利亚麦格理大学专攻音乐感知和认知(我曾经是一个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研究生助理),表明我们可能缺乏精神模板,或模式,分类这些节奏,因此无法察觉他们清楚。“节奏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比尔告诉我,“因为我的感觉是,‘听到’一种特定节奏模式的能力首先和‘预测’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是等同的。”比尔补充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模,“我们就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会有‘听不到节奏’的体验。”当然,从字面意义上说,我们‘听到’了节奏,但我们只是无法预测其展开模式。”民族音乐学家大卫·洛克(David Locke)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西非鼓乐专家,他在研究一种乐器时也有类似的经历fontomfrom由一个叫做嘎族的民族扮演。他认为,“思维缺乏组织特征”会让“甚至很难感知耳朵接收到的东西”,这与汤普森的观点相呼应。
不管原因是什么,试图破译这些简短而令人困惑的片段就像试图接住一把落下的刀。我仍然记得当我意识到我正在经历一个听觉上的盲点时,我感到的震惊。这就好像是一次高度选择性的笔划剥夺了我阅读字母Z或看到紫色的能力。那些节奏,有些一眨眼就过去了,简直超出了我的理解力。
所以,奥本是否教会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可能并不重要;就算他打了,我也怀疑我们能不能打。但问题是:为什么奥本没有承认他私下教给我们的模式不是我们期望在公共场合演奏的节奏?

一个经过一番努力,英格丽德和我设法说服了夸梅·安特维,我在大bommaa教我们在公开表演中应该演奏的延伸模式——那些Kwame Obeng甚至拒绝承认存在的模式,而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模仿不出来的模式。但这种经历只会让我们比以往更加困惑。而不是播放我们非常想听的音乐,甚至是播放英格丽德所说的“可笑的婴儿版”bommaa安特维演奏了另一种简化的变奏。安特维的课程版本比本的稍微复杂一些,但仍然不像真正的交易。然而,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安特维坚定地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是的,是一样的,”他说。
“听起来不一样了。这不是Kwame Obeng在我们的课上展示给我们的他我说。
“是的,它们是一样的!””他坚持道。
“跟什么一样?”我想尖叫。
也许问题在于大脑的代词功能fontomfrom. 如果这些难以捉摸的节奏没有语义内容,那么Obeng和安顿没有考虑他们的缺席(或在场)是否构成有意义的区别呢?这可能会使“课程模式”和“表现模式”等同于我们的教师,即使他们在我们看来显然是不同的实体。或者,也许两位夸梅是根据其他一些标准来评价音乐身份的,这些标准对我们来说就像神秘的节奏本身一样陌生。
我以为我在敲出一些无害的舞蹈节奏,而实际上我在参与一个简短的音频表演,内容是屠杀儿童的仪式。
英格丽德和我急于了解真相,于是向著名民族音乐学家J.H.K. Nketia求助。Nketia当时是加纳大学(University of Ghana)非洲音乐与舞蹈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frican Music and Dance)的主任。Nketia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来自阿善提地区的阿肯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在Akuapem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写了关于阿肯人击鼓的开创性著作。当我们告诉他简化的时候,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bommaa在我们的课上,奥本和安特维试图伪装成真实的节奏。但他还是笑了笑。
“它们可能被简化了,但它们仍然是一样的,”他说。
“因为它们有相同的韵律?”英格丽德问。
“是的,有。但不仅如此,”他说。“一件作品由许多不同的元素组成,赋予它身份。如果存在这些元素,则是相同的。如果不是,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你必须努力克服的概念。”
但是哪些元素构成了节奏的特性呢?当Obeng来到多伦多时,他教我和我的鼓手同伴们在小乐器上演奏的伴奏模式的基本版本和交替版本,把区别清楚地表达出来。然而,在阿布里,奥本甚至不承认基本的区别bommaa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的节奏——他以前在多伦多教过我的节奏,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中表演过的节奏——以及我们应该在公共场合演奏的更长、更复杂的节奏。如果我知道Obeng在每个例子中所关注的是什么,也许我就能理解它们之间的明显区别。但我不知道,也许,考虑到很难识别fontomfrom开始时,我不能。
或者,也许我们的老师只是在耍我们。

米任何非洲社会都将其传统知识保密,而这些秘密的守护者——长老、牧师、酋长——往往会逐渐披露,随着一个人通过更高层次的信任而提升,这些秘密会被零零碎碎地泄露出去。这可能是因为信息本身具有内在的敏感性,也可能是因为其深奥的本质为拥有信息的人提供了权力和威望。艺术历史学家玛丽·努特(现为玛丽·努特·罗伯茨)在她的书中写道:“对非洲秘密的研究表明,那里的秘密内容不如将秘密作为一种策略来使用重要。”《秘密:隐藏与揭示的非洲艺术》. 虽然秘密的内容可以被保护和隐藏,但秘密的存在经常被炫耀。拥有秘密知识,并表明自己知道,是一种力量
这能描述Akuapem如何对待音乐知识吗?也许奥本不愿意教我们这些缺失的节奏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某种特殊信息。也许他们的身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和其他宫廷鼓手会在公开场合演奏,但我们不被允许私下学习——这凸显了他自己的权威,以及我们作为新手的身份。
我们已经亲身经历过这种隐瞒和揭露的动态。我们一起在多伦多的那段时间,奥本从来没有跟我提过fontomfrom“说话”就像他们的大表兄弟一样。然后,有一天在阿布里,英格丽德和我在宫殿里帮奥本搬fontomfrom鼓声响起,他不经意间透露了铁钟和三个小鼓在说什么。这是一场全面展开的对话:
万人迷wobeko。
Woto wobeto。
莫夫拉马·库姆是谁?
快,快,快。
“即使你不想去,你也得去。”
“你会掉下去,你会掉下去的。”
“你把小孩子都杀了吗?”
“刚才,刚才。”
“这是什么意思?”英格丽德问。“他们为什么要杀孩子?”
奥本说:“这是关于远古时代,祖先制造‘药’。”。他接着描述了人类曾经是如何在宫殿里献祭的,这是我以前只在人类学研究和历史文献中读到的。不用说,我们都大吃一惊,尤其是我。几年来,我以为自己一直在敲打一些无害的舞蹈节奏,而事实上,我一直在参与一个简短的关于屠杀儿童仪式的音乐剧。
我不知道为什么夸梅·奥本选择了那个特殊的时刻来启发我们,但我怀疑这是否是偶然。也许,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英格丽德和我已经以某种方式证明了我们的价值。
还有一次,在一个葬礼上,我问夸梅·安特维(Kwame Antwi),他和其他许多人在凉鞋的背带上戴的那个小装饰品是否有什么意义。
“是的,”他说。
“什么?”我问。
”Aburuburuw nkosua,”他说。“这是一颗鸟蛋的名字。”
“这是谚语吗?”
“是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们得问问夸梅·奥本。”
所以我们做到了。
Obeng在Twi上回应道:“如果有文字记载,那就有文字记载;若这是神的旨意,就必成就。”
我又转向安特维。
“大家都知道这些装饰品叫什么吗?”我问。
“是的,”他说。
“但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没有。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和王室一起行动的人才可以。”
安特维是奥本的侄子和他在宫廷乐团的副官。以任何合理的标准衡量,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皇室一起搬家。但即使是他也不知道一句谚语的基本含义,而这句谚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牢牢地印在他的脚上。
音乐中缺失的复杂性是不是代表了我自己神秘的谚语,是我还没有权利去学习的东西?这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吗?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能通过自己琢磨音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奥本不愿意教我缺失的节奏,但同样不愿意明确拒绝我?
T这是我目前所能找到的。18年后的今天,事后看来,奥本行为的原因和那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一样让我难以理解bommaa当我第一次遇到他们的时候。
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训。
作为一名音乐家和民族音乐学家,我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努力,我最终会了解我们主持人的音乐和音乐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相信这一点;这样做是我自己身份认同感的核心,就像任何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做实地调查的人一样。当然,我在研究生院的导师中没有一位提出我(或其他任何人)可能会遇到一群人,他们的音乐和动机会顽固地抵制分析和解释。在这个极度互联的时代,当曾经遥远的土地离我们只有一次廉价的飞行或一个网页之遥时,人们很容易认为,跨文化理解的所有障碍正在逐渐消失;不再有陌生人这样的东西,只有我们还没有在谷歌搜索过或在探索频道上见过的人。
这是一种错觉。毫无疑问:有很多人,生活在很多地方,他们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巨大的谜题,不管有没有便宜的机票。这绝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它证明了人类的多样性和人类理解的局限性。我在阿布里的经历可能令人沮丧,但我学到了很多。我不再认为跨文化交流的所有障碍都可以克服。我也不认为我能真正地、真正地进入别人的头脑,像他们一样通过纯粹的理性和意志去看(或听)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由于这些原因,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对强度我们目睹动物祭祀和精神,遇到文化财富和物质贫困在西方,很少见到,激进的文化冲击的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又没有since-Aburi仍然充满我的时候带着一丝敬畏。我知道英格丽德也这么想。当我们谈论那些塑造了我们作为个人和夫妻的事情时,我们总会回到加纳,以及那些事情的神秘bommaa节奏。
亚历山大·盖尔芬德(Alexander Gelfand)是一名自由作家,也是纽约市正在恢复的民族音乐学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他在加纳生活的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