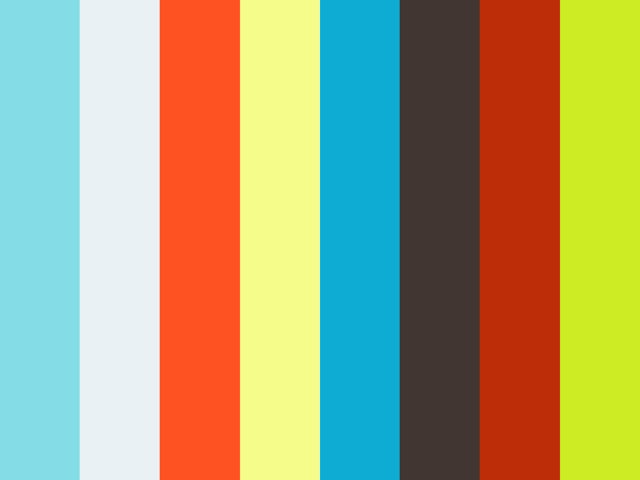O1884年7月的一天,四名遇难船员登上救生艇,向西北方向驶离好望角。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汤姆·达德利、埃德温·斯蒂芬斯、埃德蒙·布鲁克斯和理查德·帕克为了生存,用桨击打鲨鱼,喝尿液,甚至吞下一只不守规定的海龟骨头。由于地平线上没有救援的迹象,四重奏开始讨论为了团队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第二天,帕克陷入了昏迷。达力看到了一个机会,便用小刀割开了帕克的脖子。剩下的三人开始吃东西。几天后,一艘驶来的德国船只救起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回了英国。在那里,他们承认杀害并吃了帕克,被判谋杀罪,并被处以绞刑。但是内政大臣威廉·哈考特为他们减刑——达德利和斯蒂芬斯只在监狱里呆了六个月,而没有被送上绞刑架。
这是幸运的,而且幸运的是,凭借水平的Harcourt。虽然他是显然是反叛的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德利是一个英雄,因为他坚强地面对恐怖的谋杀,显然这并没有影响内政大臣对此案的判断。他表明,由于这些人被困在海上,忍饥挨饿,必须靠吃东西来生存,对他们的惩罚可以更好地针对一场不那么令人震惊、也更容易理解的谋杀,而不是冷血杀人。
然而,它可以说,回到哈尔科特的一天,对于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惩罚倾向于苛刻 - 也许是因为它保留了秩序并促进社会物种之间的合作。例如,饥饿的猕猴经常攻击那些没有提醒小组他们发现食物,可能会教导关于分享的教训;大象密封幼仔捕获从无关的女性偷牛奶往往有点,偶尔会被杀死。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看来人类的精心制定的法律机构和程序并没有显着改变我们在数十万年前发展的心理学来回应不法行为。
哈佛大学道德心理学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Fiery Cushman说:“我们在非常年幼的儿童和跨文化人群中发现,人们不希望受到伤害而不受惩罚。”即使是无意的行为,情况也是如此:2014年,一名青少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撞倒了躲在树叶堆里的两个孩子,导致他们死亡。库什曼在网上对调查对象进行了调查,94%的人认为司机辛西娅应该被监禁。但是85%的人在听到一个没有孩子在树叶堆里的故事后表示,根本不应该有惩罚。“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判断很了不起:一堆树叶里是否藏着孩子,纯粹是运气问题,而辛西娅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的论文.“然而,我们指定的惩罚金额对一个人造成伤害的程度的这种几率变化非常敏感。”
Cushman认为,当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时,“更原始的,所以说话”你造成了它,你应该遭受'反应永远不会消失。“
但是,有时候,通过了解更多的意图可以克服它。
在2008年研究库什曼发现了部分原因:不同的因素对我们很重要,一方面,当我们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允许,另一方面,当我们决定,什么是合适的惩罚,是否有人应该受到责备。他写道,道德判断“压倒性地决定”于我们对某人所思所想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否“有罪”;但我们对惩罚和责备的想法更多地与“因果责任”有关,也就是某人的行为如何导致某种后果,而不管他们在想什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实际上在决定我们的道德判断上相互竞争,库什曼总结道:“因果指责的归属竞争性地阻碍了精神罪责的归属,而对因果评估的沉默则使精神状态评估占据了主导地位。”
仁慈和理解,以及不愿给别人带来痛苦,是人性中强烈的东西
我们也经常把人们的行为作为他们精神状态的可靠代理。在2015年的一次纸尼尔·利维,牛津Neuroethics中心副主任写道:“因为有一个足够高导致之间的相关性和有意伤害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损害的因果关系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指责的充分条件。”他解释说,这里的问题是代理权可能具有误导性。库什曼表示,这导致了不合理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往往开始只关注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法律反映了更原始的反应。”例如,汉谟拉比,城邦巴比伦的国王,提出治罪法, 以眼还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Cushman表示,法律规范“获得更大,更加注重意图”。
萨福克大学法律哲学教授的奈吉·艾西比维斯表示,这是一个明确的例子,这是遭受被虐待的女性综合征的防御论点。2006年,玛丽维克勒拍摄她熟睡的丈夫,一名基督教牧师,拿着猎枪在后面,随后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逃跑了。她在法庭上解释说,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开枪(后来杀了)丈夫的动机是他多年来对她的身体和性暴力,以及虐待他们的孩子(他会窒息他们,让他们不要哭)。温克勒被指控的罪名不是一级谋杀,而是故意杀人罪;她没有被判25年到终身监禁,而是在监狱里待了一年,接受了60天的心理咨询。
这不是一个伸展,即使只是几十年之前,Winkler也会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但今天,在像Winkler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可能会考虑虐待关系的背景。甚至是生命如何展开的背景。遵守“历史记叙者”的想法,“差写的故事描述了一个人是如何成为她的人,”在Lehigh大学的道德心理学家和一位同事中写下迈克尔·吉尔研究发表在3月。他们发现历史决定论的叙述“减少了对违法者施加恶意惩罚的冲动,但保留了非暴力引导违法者走向道德进步的冲动。”
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向实验对象提供了不同的信息,解释为什么罗伯特·奥尔顿·哈里斯在1978年杀害了两名十几岁的男孩。其中一组收到的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的故事,描述了一段困扰和被虐待的过去,而另一组收到的是捏造的信息,说哈里斯生来就有大脑缺陷。(他们告诉另一组控制组,只说哈里斯杀了男孩。)研究人员发现,听过历史主义者叙述的受试者承担的责任最少,因为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叙述降低了受试者对哈里斯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他的“自我形成”的印象。
吉尔说:“责备和惩罚的责任和惩罚的冲动显然是强烈的“你在法律制度中所看到的是这两个动机之间的持续冲突。”
Matthew Sedacca是一名编辑实习生鹦鹉螺。
最新和最受欢迎的文章投递到您的收件箱!
观看:Simon Dedeo为什么他开始数字化英格兰的旧犯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