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令人好奇的是,三月的英国拒绝为应对全球大流行,采取重要的保持社会距离措施。政府接受了几个团体的建议,其中包括所谓的“助推单位”(Nudge Unit),这是一家名为“行为观察团队”(Behavioral Insights Team)的私人公司,该公司利用行为科学为英国决策者提供如何“推动”人们采取某些行动的建议。据报道,英国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引用“行为疲劳”,即公众对这些措施的承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这是政府会议中的一个政策问题。尽管实验心理学家David Halpern领导的轻推小组的想法受到了挑战,但这形成了该国的大流行反应。*宽松的措施不仅引发了关注病毒传播的流行病学家的强烈反弹,还引发了600名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弹,政治科学家等等。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公开信怀疑导致政府决定的证据的质量。
值得政府赞扬的是,有一些证据但这可能还不足以让它成为一个国家应对致命流行病的基础。正如Anne-Lise Sibony,一位研究法律和行为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员所说,写的在欧洲风险管理杂志他说:“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行为疲劳单独挑出来,因为其他有更好记录的行为现象——同样未知的概率和分布——可能在起作用,或者助长或抵消它。”
英国最终屈服于压力。加速通过禁止大规模集会、要求任何有COVID-19症状的人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以及鼓励人们避免不必要的旅行和接触,努力减缓病毒的传播。但关于行为科学应该如何以及何时塑造公共政策的争论仍在继续。
“事实是,这个价值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已经远远超出了证据的范围。”
缺乏疫苗意味着我们应对流感大流行的最佳对策是改变我们的行为。为此,由心理学家杰伊·范·巴维尔(Jay Van Bavel)和罗布·威勒(Robb Willer)领导的一组行为科学家发表了一份纸在里面自然的人类行为关于社会和行为科学如何支持对大流行的应对。它强调了科学传播、道德决策、压力和应对等主题的研究。研究人员写道,这篇论文的目的是“帮助人类行为与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保持一致”。例如,作者指出研究这表明,强调共同的社会身份可以帮助群体应对威胁,并鼓励遵守社会规范。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建议公共卫生官员传播信息,让人们感受到与当地社区或同胞的联系,这可能会有所帮助。
如果像这样的见解使人们更有可能采取建议的预防措施,这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那么为什么呢不应该我们听行为科学家的吗?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所说评论在美国,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考虑心理因素,“他就不会因此避免心理因素。”相反,他会强迫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将是一种糟糕的心理。”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坏的心理学来自科学家。“如果我们对无法复制的研究过于自信,”心理学家汉斯·艾泽曼(Hans IJzerman)告诉我们鹦鹉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然后我们也在建立自己的心理。”在黄金时间之前使用证据可能并不比什么都不使用要好——这可能会浪费资源,甚至对那些它想要帮助的人有害。例如,对行为疲劳的担忧本来是为了保护英国公众,但最终却通过延迟社会距离间接促进了病毒的传播反倾销措施。
行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已经有了一个长期而深远的历史广为人知与质量控制作斗争。许多有影响力的实验在进一步审查后都没有成立,通常是由于小的和非代表样本,草率的数据分析,以及高度特定于上下文的发现。这暴露了行为科学在如何进行和解释方面的系统性缺陷,使其成为任何公共政策的不可靠基础。“作为一个从事研究近20年的人,”写的研究自我控制的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英兹利希特(Michael Inzlicht)说:“我现在不禁想知道,我选择研究的主题实际上是否真实而有力。这些年来,我是不是一直在追逐一缕缕烟雾?”
心理学和其他领域在解决自身缺陷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行为科学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烟雾。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反对种族主义警察的抗议活动之后,人们重新燃起了利用科学改变警察行为的兴趣。多年来,隐性偏见培训——旨在帮助参与者认识和抵制自己的歧视性想法和感受的课程和研讨会——一直被奉为解决问题的良方,不仅适用于警察部门,也适用于白领办公室和其他许多职业环境。但问题是似乎不是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下是有效的。一个2019荟萃分析研究发现,虽然某些干预措施可以减少内隐偏见,但它们对改变人们的行为没有多大作用。“事实上,这个价值数百万美元,或许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已经远远领先于证据。”说Patricia Devine在《市场晨报》上主持了一个研究偏见的实验室。
另一个基于行为科学的政策出错的例子是一些教育研究人员称之为“教育炒作周期”,其中“在实验中产生积极结果的有希望的想法被简化,并被吹捧为‘答案’。”写的心理学家David Yeager。“然后教育者或决策者不加区别地应用它们,就好像它们是杰克的魔法豆,无论它们种在何处,都能让学生振作起来。”以“学习风格”为例:许多教育工作者被鼓励将他们的学生识别为视觉、听觉或动觉学习者,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教学风格,但这一概念并不明确铺位.
决定是否将政策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归根结底是在根据不完善的证据采取行动的利弊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有一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政策的潜力可以巧妙地补充人类行为的许多怪癖,比如由推动部门制定的干预措施增加税率和器官捐赠,或使用精心设计的海报改善手部卫生在卫生保健工作者。但许多研究人员仍宁愿谨慎行事。
在预印本回应在范巴维尔和威勒的论文中,艾泽曼和他的同事呼吁行为科学家更加谦逊和克制。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证据准备水平”的系统,他们称之为“标记可信和可操作的研究结果的指南”。该系统基于类似的系统证据准备水平包括从1级的初步观察到9级的现场测试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在危机中部署。
我们可以想象,证据准备水平框架对于(比如)防止另一个教育炒作周期或向无效的隐性偏见培训注入公共资金真的很有用。但在流行病期间,当公共卫生官员被迫尝试改变人们的行为时,不管有没有来自beh的投入,情况会怎样航空科学?
生物伦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米歇尔·迈耶(Michelle Mey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不确定(火箭科学)是否总是行为科学的一个好的比较对象,即使是在疫情期间部署的行为科学。鹦鹉螺. “我不清楚我们是否需要登上月球,但我们确实需要向人们传达关于如何在流感大流行期间保护自己的公共卫生信息。无论如何,这一信息发生的条件是,为什么不借鉴行为科学的观点,开发一些不同的信息,并测试它们,看看哪一种最有效?”
其他证据评估框架也已建立提出了但是,无论行为科学家采取哪种方法,都必须回答同样的难题:什么程度的不确定性是可以接受的?即使是最稳健、重复性最好的行为干预措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因此,在行为科学家就灰色区域的大小达成一致之前,公共卫生官员、教育工作者和所有其他寻求行为科学见解的人可能只需要自己做出决定。
斯科特·柯尼格(Scott Koenig)是纽约市立大学神经科学专业的博士生,在那里他研究道德、情感和精神病。在推特上关注他@斯科特科尼.
最新和最受欢迎的文章投递到您的收件箱!
观察:为什么心理学家经常将他们的研究视为“自我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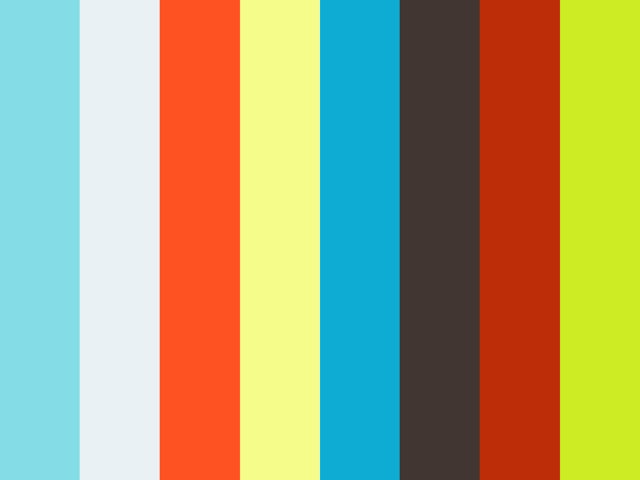
*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错误地将对“行为疲劳”的担忧归因于轻推单元。我们对此错误表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