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昨天去邻居家吃东西了。
想想这个句子。非常简单,说英语的人会准确地知道它的意思。但它实际上告诉了你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了你什么不告诉你什么?它没有具体说明一些事实,比如主题的性别或邻居的性别,或说话者的方向,或邻居的关系的性质,或食物是饼干还是复杂的咖喱。英语并不要求说英语的人提供任何这些信息,但如果句子是法语的,每个人的性别都会被指定。
几十年来,不同的语言传递信息的方式一直吸引着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本杰明·李·沃尔夫的化学工程师出版了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书纸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该研究认为,语言表达性别、时间和空间等不同概念的方式影响了说语言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如果一种语言没有表示特定时间的术语,说话者就不会理解时间流动的概念。
马西斯家的人说话似乎很谨慎。
这一论点后来被质疑,因为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它夸大了语言对我们思想的限制。但研究人员后来发现,这些说话习惯会以更微妙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描述这条调查线是这样的:“语言本质上是不同的必须传达,而不是传达五月传达。”换句话说,语言影响我们思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它迫使我们思考什么,而不是阻止我们思考什么。
这五种语言揭示了信息是如何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表达的,以及这些思维习惯如何影响我们。
一种你不是世界中心的语言
说英语的人和其他人在定位自己的世界时都是高度自我中心的。物体和人存在于你的左边、右边、前面和后面。你相对于你所面对的方向向前或向后移动。对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一个名为Guugu Ymithirr的土著部落来说,这种“我我我”的空间信息方式毫无意义。相反,他们使用红衣主教的方向表达空间信息。所以比起“你能挪到我左边吗?”他们会说:“你能搬到西部去吗?”
语言学家盖伊·多舍尔(Guy Deustcher)表示,说Guugu Ymithirr语的人有一种“内在指南针”,这是在极其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印记。就像说英语的婴儿在说话时学会使用不同的时态一样,Guugu Ymithirr语的孩子也学会了沿着圆心线而不是相对于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方位。事实上,杜舍尔说,如果一个说Guugu Ymithirr语的人想要把你的注意力引到他身后的方向,他“指向自己,就好像他是稀薄的空气,他的存在与他无关。”这是否会转化为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辩论。
其他的研究已经所示使用基本方向来表达地点的语言的使用者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事件的经历是如此清晰地由事件发生的方向定义的。但Deutscher很快指出,仅仅因为他们的语言没有定义相对于交流的人的方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理解背后的概念,例如。
一种时间从东流向西的语言
斯坦福大学语言学家Lera Boroditsky和伯克利大学的Alice Gaby研究了Kuuk Thaayorre语言,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Pormpuraaw人说这种语言。和Guugu Ymithirr一样,它用基本方向来表示位置。但是Boroditsky和Gaby发现在Kuuk Thaayorre中,这也影响了说话者对时间的理解。
罗塞尔岛的居民把颜色作为隐喻的一部分。
在一个系列在实验中,语言学家让说Kuuk Thaayorre的人把一系列的卡片按顺序排列——一张是人在变老,另一张是鳄鱼在成长,还有一张是人在吃香蕉。在实验过程中,演讲者坐在桌子旁,一次面朝南,另一次面朝北。不管他们面对的是哪个方向,所有的演讲者都是按照从东到西的顺序排列卡片的——随着一天的过去,太阳穿过天空的路径是相同的方向。相比之下,讲英语的人在做同样的实验时,总是按照我们阅读的方向从左到右排列卡片。
对说Kuuk Thaayorre的人来说,时间的流逝与基本方向密切相关。博罗迪茨基写道:“我们从未告诉任何人他们面对的是哪个方向。”“Kuuk Thaayorre人已经知道这一点,并且自发地利用这种空间方向来构建他们对时间的表征。”
一种颜色是隐喻的语言
人类看到的世界是在一个特定的光谱里,如果你有完全正常运作的视网膜视锥细胞,光就会分解成各种确定的颜色。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说法,所有的语言都有一套特定的颜色术语来划分可见的颜色光谱。人类学家布伦特·柏林和语言学家保罗·凯于1969年提出“基本颜色条款”他认为所有的语言至少都有表示黑色、白色、红色和暖色或冷色的词语。
Yélî Dnye的情况并非如此。2001年,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史蒂文·莱文森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语言人类学杂志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罗塞尔岛上出现来反驳柏林和凯的理论。罗塞尔岛居民说Yélî Dnye语,这与邻近的其他语言群体非常不同。它几乎没有专门的颜色术语——事实上,没有专门的词来形容“颜色”。相反,说话者将颜色作为隐喻短语的一部分来谈论,颜色术语来自于岛民环境中物体的词汇。
例如,要形容某物为红色,岛民会说"mtyemtye,源自于mtye或“红鹦鹉种”。另一个例子是mgidimgidi,可以用来表示某物是黑色的,但它直接由表示夜晚的单词衍生而来。mgidi莱文森写道,不仅如此,岛上居民的语法也强化了这种隐喻倾向,说“这个人的皮肤像鹦鹉一样是白色的”,而不是“他是白色的”。
他报告说,在他们的艺术中,岛民不倾向于使用非自然的染料或色调,坚持使用中性色调和图案作为装饰手段。这并不意味着罗塞尔岛居民以某种方式进化出了与其他人类不同的视觉能力,但这可能对他们诠释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当然会影响他们如何描述它。
一种让你提供证据的语言
在秘鲁的新圣胡安,马蒂斯人说话时似乎非常谨慎,确保他们交流的每一条信息都是他们在说话时所知道的真实信息。每句话都有不同的动词形式,这取决于你是如何知道你所传达的信息的,以及你上次知道它是真实的是什么时候。
例如,如果问你:“你有多少个苹果?”然后,一个说话的人可能会回答:“上次我检查水果篮的时候,我有四个苹果。”不管说话者有多确定他们还有四个苹果,如果他们看不见它们,那么他们就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说的是真的——就他们所知,一个小偷可能偷了其中三个苹果,那么信息就不正确了。
语言中有大量用于描述信息的特定术语,比如在最近或遥远的过去推断出的事实,关于过去不同时间点的猜测,以及作为记忆重新叙述的信息。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语言学家大卫•弗莱克(David Fleck)撰写了他的著作的博士论文马蒂斯的语法。他说什么说mateses有别于其他语言要求演讲者提供证据对他们说的是,说mateses一组动词结尾知识的来源和另一个单独的方式传达真实,或有效的信息,如何确定它们。有趣的是,没有办法表明一条信息是传闻、神话或历史。相反,讲话者将这类信息作为引用,或者作为在最近的过去推断出来的信息。
一种没有“二”字的语言
2005年,曼彻斯特大学的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亚马逊土著部落Pirahã人的语言的研究当代人类学.在书中,他详细描述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语言的语言。Pirahã说的是一种没有数字、颜色术语、完美形式或基本数量术语的语言,比如“少数”或“一些”——有些人认为这些术语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比如颜色。Pirahã表示的是某物的大小,而不是使用“每”和“更多”之类的词或编号的数量来给出数量信息。有一个词大致翻译为“许多”,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聚集在一起”。Pirahã也没有艺术传统,也没有深刻的记忆。
史蒂文·平克著名的被称为埃弗雷特的论文"扔进派对的炸弹"埃弗雷特发现了一种语言直接反驳乔姆斯基被广泛接受的普遍语法理论。
在一个系列在语言学家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埃弗雷特(Everett)等人的实验中,Pirahã的认知能力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检验:没有数字系统,数字认知是否可能?答案似乎是“不是真的”。在埃弗雷特的一个实验中,科学家向Pirahã展示了一排排的电池,并要求他们复制这些电池。他们能够重建包含两到三个电池的排架,但什么都没有上面.Pirahã没有使用计数,而是使用了埃弗雷特称之为“模拟估计策略”的系统,该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很有效。可能是Pirahã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计算才能通过埃弗雷特和其他观察过Pirahã的人肯定认为是这样的。
有趣的是,Pirahã似乎对局外人并没有很高的评价。他们只会说一种语言,更喜欢使用自己的词汇,而不是从英语或西班牙语中借用词汇,他们把所有其他语言都称为“歪脑袋”。这与我们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的社会以全球化的语言为基础,所有的交流方式都被翻译成数字——无穷无尽的1和0。
克莱尔·卡梅伦光谱参与编辑。在推特上关注她@ClaireHCameron.
最新和最受欢迎的文章投递到您的收件箱!
看:传奇作曲家沃尔特·默奇谈到贝多芬如何改变了音乐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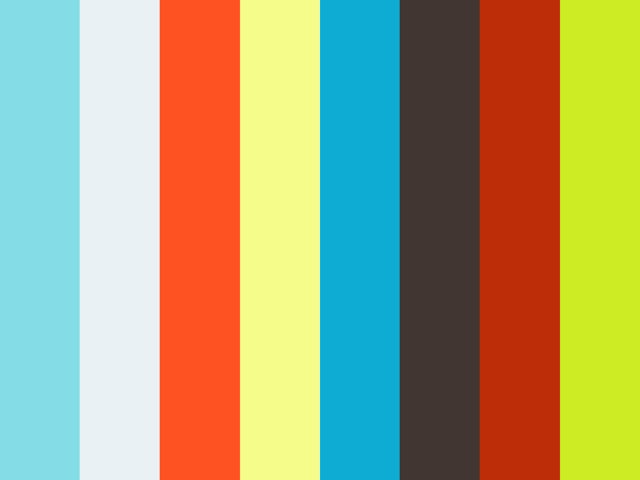
这篇经典的事实如此浪漫的文章最初发表于2015年3月。

















































































































